母权人物形象书写笔法对比分析
对比强调二者共性中的差异性,即两两对照的书写笔法。
《文心雕龙·丽辞》将丽辞分为言对、事对,而反对之出于事对在于“理殊趣合者也”[[1]],也即所谓反对是以不同的主题开展而产生相同的艺术张力。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文学代际相承,但凡是深刻而委婉的文学经典都依托于传统资源的先在经验而展开叙事,传统文学的集成、解构和重建是文学内部记忆一种颇具血脉相承的记忆延续。
故而,不论是文本的体裁样式、结构章法、情节架构、话语形式、风格等等要素都不免流露出前人的痕迹。 然而,作者的一切创造,“把他人话语作为文化符号引入自己的文本,引入话语或结构,其目的是为自己的个性化命题服务” [ [2] ] 。
其实,这些对于人物描摹同样适用,明清家庭题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凝结着传统文学的多元滋养,但绝非对传统亦步亦趋地跟随,而是不拘于拆解传统,建构其自身独特的人物群像。
本节通过将传统的叙事艺术和明清家庭题材小说中之母权人物作一比照,着眼于母权人物形象与历史镜像之同类异构的叙事艺术作出分析。
《文心雕龙》书影
一、 从角色到人物
角色最初与“脚色”同义,均指“履历状”,“角色”与“脚色”二词其初始意义基本上一致,且随着元代夏庭芝在《青楼集志》对传统戏曲脚色行当的划分,而随之确定舞台扮演的形象类型而脚色概念随之定型。
脚色常见于元代杂剧之中“脚色代指戏剧行当,是根据戏班演员的技艺工种进行区别;角色则指代剧中的各类人物形象”[[3]]。
此处,角色涵盖了脚色中的行当,也就成了一脚(生旦净丑登)扮演多个角色的情况,随着戏曲艺术的完善和发展,角色再次发展以至于替代“脚色”的体认功能,意义进一步延申,成为广义上的“类型”形象,譬如“主角”和“配角”,即是角色对涵盖身份意义上的指认。
而人物则不同,人物剔除了角色中的类型化特征和文化符号的代称,而赋予了更多的性格因素,相比于角色的程式化和固定性,人物显示出其独立性和形象建构的立体性,是“人”和“符号”的本质区别。
就形象本身来看,人物也需要扮演角色,然而人物有其形象的或多或少的性格化特征,人物既“凝结着丰富的社会心理文化内涵”又在“具体的情节结构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4]],而丰满完整的人物正是随着明清叙事文学的繁荣发展而强化其核心地位的。
(一)人物形貌——丰满完整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一书中提到:“人的思维过程都受制于普遍的法则,这些法则最清楚地体现在人类的符号功能之中。”[[5]]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总是记忆惯性地延续一些模式化的角色去表达某种价值认同,如好人和坏人的角色则代表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喜恶”的价值取向。
然而“人物”在建构过程中则打破了传统叙事意义上单一文化符号的形象表达的可能,而是力图从多个方面来建构独特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审美和区别化的人物群体。
这体现在明清家庭题材小说中母权人物形象的形貌的刻画上,则呈现出丰满、生动的个性化的特征。
远古神话作为小说的胚胎和萌芽而存在,其结构、情节以及人物虽然略显粗略,但其背后所包孕的文化精神、神异主题和浪漫化气息都为后来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影响了小说叙事形态,成为小说之雏形和发端。
上古神话“女娲”和“西王母”形象构成了以后叙事文学作品中母权人物原型的集体想象,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延续下来。
《结构人类学》封面
纵观整个文学史,其中较为典型的母权人物书写在各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上古神话、历史散文,志人小说、长篇叙事诗以及之后的唐人传奇、宋元笔记小说和戏曲等都有关于母权人物的零星叙写。
尽管母权人物已经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视野中活跃了几千年的历史,然而,直到明清叙事文体小说的兴起和鼎盛,才将这一历史性的人物给写活,其人物群体之集中,形貌刻画之细腻,艺术形象之丰满和完整,这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人物形貌刻画重在外貌刻画,主要依托容貌、体态、神情、服饰等等外在特征刻画人物,这样细致的刻画很少出现在一些抒情性作品中,而以叙事文学见长。
母权人物原型之一女娲形象在先秦典籍中以“女娲有体,孰匠制之?”[[6]]对女娲形体进行探源,并未出现丝毫刻画痕迹。
郭璞注“人面蛇身”[[7]]点明了女娲的形体特征,其他譬如《淮南子·览冥训》、《风俗演义》等对女娲的记述都只是叙述了其作为母神补天、造人的拯救守护神神格特征,并未对其外貌作整体性陈述。
对于西王母的外貌特征,《山海经》中仅仅以“状如人”和“虎齿豹尾”的外貌一以概之,在上古神话故事中,形象的概括是相当粗线条的,并不足以作为建构独特的“人”的功能,人物还停留在粗陈梗概的单一的叙述层次,也仅仅是点明了其扮演的身份——角色的层面。
尽管在《史记》《战国策》这类书中对一些权力太后有过刻画,但也是对其行为本身,更加注重对言语的表达去描摹人物,故而外貌也不是刻画人物的重心。
在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形象是母权人物形象中较为典型的角色,然而文中始终没有对其外貌作过直接的陈述,文中仅用“怒”的神态有所披露,细致的形象刻画几乎一片空白,处于“受叙”者的立场,“阿母”点明其身份。
至唐人传奇中,则多以“老妪”代之,人物并不时时出场,只是代为交代。
而至宋元戏曲,尤其是戏曲艺术走向成熟的元杂剧,人物塑造为之一新, 《西厢记》的崔老夫人郑氏俨然一个包办女儿婚姻、捍卫封建礼教家长的典型,较之于前期叙事作品中人物形象有了巨大的进步。
尽管如此,作者也只是开场交代了其子母孤孀和相国夫人的身份,从其性格、语言行为等方面着力于其人物特征,并未从形貌上多下功夫,及至于明清小说的出现,人物方才于同一中显出差异来,形象更为丰满立体,而有“一人千面”的形象特质。
《西厢记》简介
明清以来的小说确实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笔者所讨论的对象——母权人物也在小说中密集地展开叙述,这在以往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
相对于以往叙事文学作品,母权人物仅仅作为一个角色出现,作者仅仅被之权威的母亲身份,其叙事声音往往也是被动乃至缺失的。
类型化的甚至是雷同的母权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化符号式的记忆被反复叙写,这样的叙事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清通俗叙事文学小说、戏曲的成熟,母权人物才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
的确,相对于明以前母权人物的孤立和符号化的单一性,明清以来家庭题材长篇中的对母权人物的刻画更为集中和关注。
这在于以往古典文学作品中多对于才子佳人形象的刻画,由于审美价值在于对既定的美的体认,沈士龙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之形体美作了总结“自古以文字类写娟丽……皆妙于形容,亦足写一时之艳。”[[8]]
其实,在《诗经》、《离骚》中多有对貌美女子“窈窕”形体的熟练表达,这不足为怪。
古代的叙事文学均延续了“男才女貌”的人物叙写方式,故而“女子貌美”的形体叙事往往更多地将焦点建立在对妙龄女子形象的关注,像任氏、霍小玉、崔莺莺、李娃等唐传奇中的少女刻画就非常的生动,而很少对母亲或者说年老色衰的妇女形象进行集中而紧密的外在形貌的刻画。
明清家庭题材小说的出现方打破这一传统,不仅让女性披甲上阵,代父执权,家庭题材的介入使得小说将笔墨更多地集中于对家庭人物进行书写,那么被赋予权威的母亲形象获得了更多书写的空间。
清人沈宗骞云“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故形或小失,犹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则竟非其人也。”[[9]]
故而形虽有不同,但可言陈其共性,若只是追求形同,则难以区分故而言形需要追求其形貌之同而直追其神形之分离,意在形象要传神摹态。
而明清时期小说中无论人物的刻画还是人物时空场景的展现描摹都较前期小说成功,人物形象内心情感和形体形态等的融合统一将人物从角色的单一性中抽离出来,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完整。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丁锡根 编著
(二)人物性格——立体多元
人物是叙事文学的核心,叙事总是和人联系在一起,叙事目的也是为了叙人。然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塑造出性格鲜明的形象是叙事文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10]]。
金圣叹在探讨《水浒传》人物论之时肯定了人物性格塑造的重要价值,金圣叹颇为赞叹其写人功力,哪怕是“一八八个人的性格,真是一百八样。”[[11]]
成功的人物书写在于其个性化和典型性,而这些都离不开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虽有体貌和身份相似之处,却因人物性格各异而显出差异和新奇,性格越鲜明,其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就越突出,而这个人物所凝结的社会心理文化信息也就越丰富,其集结的社会内容就愈充实,也就愈加接近现实中的“人”。
其实,人物叙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角色来承担,比如说佛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显然,圆形人物也在承担人物性格展现和人物的内涵延续性方面表现得更为丰富,其相较于作品中的扁平人物更具区分性。
叙事文学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是方方面面的,形体、神态、动作、心理、语言等等都是人物性格的一个侧面,皆可塑造。
在《史记》中有一些权力太后的写照,司马迁单独为其立传,并点明她们的性格属性,譬如“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在史书中的男性化的刚毅气概在此奠定,其“佐”、“诛”的正面行为不仅在于展现其权势和政治野心的一面,同时也刻画了其性格中“强势”且 “狠辣”的特点,而司马迁“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2]]
对吕后赏罚分明、政治晏然的政绩加以称善以历史的眼光臧否人物无疑显露出强烈道德评判的倾向,其在批评之时力求与历史事件相平衡,构成人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多元价值观,显示了其在人物性格构建中的进步因素。
不过此时的母权人物尚不能构成“圆形”人物,此外唐传奇《崔书生》的崔母、元杂剧《西厢记》的崔夫人以及文人笔记《浮生六记》之沈母大似沿袭了《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影子。
以封建礼教的捍卫者自居,在儿女婚姻方面施加影响,《三国演义》中孙权之母、徐庶之母,一个是安邦定国之才,一个是忠烈骁勇之辈,都是女中英雄。
当然这和《杨家将府演义》中挥戈披甲、在沙场叱咤风云的佘太君之忠勇颇似,这些母亲形象虽说其人物性格已经相当鲜明且生动,在母权人物的文学书写史上也堪称经典。
但是,我们始终未看到像明清家庭题材小说所刻画的母亲形象之丰富多样、立体多元。
《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段江丽 著
明清家庭题材小说极为重视人物的书写,从题目多以“人物”命名方可窥见一二,譬如《金瓶梅》、《林兰香》、《红楼梦》,几部书都是取书中主要人物的名字捏合成作,作品叙事中心也几乎是围绕着人物进行铺陈叙写。
后之书多见仿效。小说文本之类的母权人物形象在一书往往对其加以集中书写,甚至同一篇文本中出现几个同中有异的母权人物,且作者都以较多的笔墨对其尽情刻画,横纵对比、正写影写等多种手法加以叙述,人物不仅展现出多重组合的类型化和个性化相结合的典型性格特征。
《三国演义》在小说人物塑造的特征化性格较为出色,其“状其形至绝”而至于失真是其塑造人物性格类型化特征最为典型的体现,其“三绝”贤相、名将、奸雄的典型人物的类型化特征几乎贯穿全书,而明清家庭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则不同,其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不是单一类型的扁平人物。
作者在人物塑造中显示出驾驭“母权人物”的本领来,同样是写权威的女性人物,女性家长和小妾性格不同,而家长与家长、妾与妾之间又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来。
石麟先生在对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进行审美观照时认为真正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应符合几条标准: “ 第一,处于书本现实之间的融合性;第二,多有令人不解之独特性;第三,性格的复杂性;第四,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 [13] ]
所谓圆融性、独特性、复杂性和唯一性都是在强调人物身上的兼容性,人物正因为融合了万般复杂的个性特征而显出独特、唯一的特性来,从而对人物的美学精神和审美功能都具有加持意义。
恰如“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14]], 人物就像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容器,善良、罪恶、狡诈、狠辣都一切善和非善的特质都整合于其中。
这正是明清家庭题材小说中人物错综复杂性的体现,人物之间、人物自身都是相互补偿,这绝非单一的好坏善恶可以衡量,明清家庭题材小说在最大程度上突破了这一点。
厉平在论及《金瓶梅》人物塑造之时道及其“人物形象呈现出由扁平向圆形过渡的趋势”[[15]]。
自《金瓶梅》问世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实现了质的飞跃以及在人物刻画方面的巨大转折,其人物塑造基本上摆脱了类型化特征而展现出性格化和个性化倾向。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封面
另外,小说还实现对原先帝王和重大历史叙事的反叛,人物不再是惊天动力、叱咤风云的大英雄,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平凡世界有思想情感的“普通人”,此即深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奇之奇”的美学思想贯穿在人物塑造的全过程。
其以后的家庭题材小说,《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基本都承续了这种写作模式。
譬如《金瓶梅》中妻妾六人均各个不同,就是看相一事都各人特特表现出差异来,月娘首先上来与众妻妾同看,其主母之万人不敢当先展露无遗,李娇儿自己过来,孟玉楼是月娘叫过来,到了潘金莲,是再三推之才出来,李瓶儿是西门庆令其相,雪娥是月娘令相,种种情状,把妻妾六人的个性活活刻画出来。
除此之外,荡秋千一折、瓶儿生子一折、佳人笑赏玩灯楼一折,各人俱有情状,人物之风情、个性在妻妾六人的形貌、行为、动作、语言中凸显出来。
其笔下人物形神兼具,张竹坡慨然称之“为众脚色摹神也”。而且《金瓶梅》中人物呈现其唯一性乃至融合性,更有让人“囫囵不解”的独特性,体现出其情理兼全而又与现实贴合圆融且符合人物美学的多重组合的人物典型。
且论吴月娘,便有冷面善心、贤德良善与敏感易妒、伪善奸险复杂个性的合一;而潘金莲又有善搬是非、淫荡浮浪且又与纯真率性等美好品行交织渗透的个性特征,作者又一大手笔庞春梅则在西门庆之身前身后呈现出正色持重和纵情声色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情。
这些人物性格呈现出多元性、立体性的个性特征,既相矛盾对立而又圆融糅合,统一到人物身上就形成了生活中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复杂化的“人”的性格特征。
这种人物美学艺术同样在其后的家庭题材长篇小说中之母权人物身上践行并施。《红楼梦》中的贾母既凌厉威严又慈祥厚爱,王熙凤既重利盘剥、心狠手辣却爱恨分明、进退有寸;《林兰香》之燕梦卿虽拘于礼教但是却忠爱有度、才情兼得的流露。
在这些人物个性和共性的一面,我们难以用某种评判尺度对人物作一定性,这正是“人人一个身段,一番谈吐”且至于人人各有一面、多面,而相似、相近、不似、远极、个性、共性、矛盾和统一等等多元化且极具兼容性的立体人物付诸笔端,定然尽脂砚斋评贾宝玉“说不得”[[16]]之妙。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欣赏》封面
(三)人物语言——雅俗并用、范中求避
文学常常以语言之巧妙,择取语言而临摹生巧、笔下生神以为塑造形象、创造典型。
“文学作品中形象的大厦,从根本上说是由文学语言的形象性构成的,即以形象的语言作为砖瓦建构的”[[17]],读者对于一部小说的人物的审美观照,基本是从一部小说外化的表现形式——语言艺术开始的。
从小说语言的出发主体来看,大体上分为两种,分别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叙事语言多由叙事人表述而出,而人物语言多通过人物对话表现。
关于叙事语言,是一部小说语言整体的风格呈现,显露出创作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惯用的风格,而这些语言痕迹往往也作用于人物语言的表达。
就整体观之古代小说之语言体系,则有“文言”、“白话”以及“半文半白”三种。譬如唐宋之前国史叙事《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至唐人传奇一类,则多以文言见长,故书多流丽庄重,至于宋元话本、杂剧戏曲一类,则以通俗取之,故庄谐参半,情致委婉。
正如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所述:“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18]]。
冯梦龙肯定了小说运用通俗语言的特殊表现力,这确乎是文言小说力求尽情模拟形状所不及的,而《三国演义》中“言不甚深,文不甚俗”的语言表现即是这种通俗语言的妙用。即便是戏曲这种通俗的叙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与小说的语言表现相媲美,虽然小说中不乏戏剧因素的渗入。
比如,小说描绘人物除了人物之间的对话之外,还有人物以外的叙事者的插入,人物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共同构成一张扩充小说的张力网。
然而,戏曲却受限于舞台的表演艺术,往往叙述人很难在人物之间横插一脚,比如通过叙事人表述虚拟的情景、人物的心理状态等等,这些在戏曲中都很难铺陈开来,虽然在刻画人物时冲突明显、情节紧凑且张弛有度,然终不及小说之细腻含蓄、娓娓道来之情致。
《晚清文学丛钞 · 小说卷》封面
然而小说的语言运用从风格上切近则区分雅俗,雅俗之辩历来是文学史上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命题,雅俗涉及到古典文学之诗、词、文、戏曲、小说等多个领域。诗之《雅》至魏晋风度;
元白诗派所发动的新乐府运动倡“浅近平易”的诗歌语言;从柳永词以俚语入词再到姜夔词“清刚醇雅”的化俗为雅,雅俗成为文学语言的一种审美哲学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传达出创作主体审美思辨的主导价值观念。
然姚侯聘评《济公传》一书言及:“言表非诸浅近,其言不足以感人;事不设神奇,其事不足为垂训。盖圣经贤传,原道义所攸关;而野史稗官,尤雅俗所共赏也。”[[19]]
其强调语言之深切动人以及奇事奇人,以奇文叙奇事,奇事显出奇人,其中最关键的在于“雅俗共赏”,这正为明清以来之通俗小说关目,这也是好的小说作品常常较于一些“雅”文学更脍炙人口。
所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20]], 现今说部之通俗浅近,较之史传而能成诵,这正是作为通俗文学的“小说易传、国史不易传”的写照。
纵观古代叙事作品之中,以宋元为分水岭,观之宋元以前,其人物语言多以雅正为能事,而宋元以后则以俗为标榜,然而真正做到雅俗并重的则在于明清集大成之作《红楼梦》之中。
其实,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就有雅俗之分,则张生语言之文雅生动,一谦谦君子形象跃然纸上,而郑恒语言则粗鄙下流则一无耻浪子浮诸笔端,然文中以雅为最,且一概才子佳人小说中均有雅俗之人事,均以雅为牵强附会居多,则明之有《水浒传》中鲁智深之粗鲁狂语,李逵之憨直蛮横语“写一百零八人,各有其声口”(金圣叹评)。
然皆以俗为主,故而其语言艺术均不如明清家庭题材小说中之雅俗并重相谐为妙。
《醒世姻缘传》中语言多以山东方言为主,故俗语运用较多,清人东岭道人之评则点出作者无意于寻找音律声色以遣词造句,而仅以浅近的语言来行文,文中多出运用地方土语而不显喧宾夺主之弊“本传造句涉俚,用字多鄙,是为得之。” [ [21] ]
《醒世姻缘传》虽处处用方言俗语以呈其趣,然而,作者亦每每以诗作为回评而妆点雅情,不可不谓雅俗之共赏。
《醒世姻缘传》封面
并总览明清以前之母权人物的语言特征,总皆不过一雅到底,一俗到底,到底不如明清家庭题材中人物之庄谐并重,在不同环境、心理状态之下有不同语言表现,共同作用于“一人发一人之议论”的前后统一的人物性格发展理念。
《金瓶梅》中吴月娘扫雪烹茶,向天祈祝,此处用雅语,而当吴月娘数落西门庆时候则用俗语:“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裏水……清潔了些甚麼兒?”[[22]],
活泼的俚词俗语增加了文字的鲜活性和表现张力,甚至方言俚语的时时插入以构成诙谐之色调,这自然冲淡了吴月娘作为主母的端庄和典雅色彩。
而庞春梅在西门庆死后抱着“且风流一日是一日”的人生俗见,却在重游西门府邸之时触景生情流露出物是人非的雅意。
《林兰香》之燕梦卿于爱娘断壁合诗,此为雅情雅语,而嫁于耿朖之后将作诗、弹琴、写画等等雅事一概不论,并在耿朖以此为风流韵事时以“修身齐家”之语规箴此其“俗言俗语”矣,此皆人物所展现出来的雅俗并置而圆融的和谐画面。
在以往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一部作品所展现的母权人物语言基本上趋同如一,诸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其语言大多是自己怒态的心理呈现,专横暴躁的性格是焦母这个人物的性格整体表征,就连与其同处母尊地位的刘兰芝之母也是不顾女儿之心志,专横将之许以太守“莫令事不举”之语,虽非一体,实质同一。
《三国演义》徐庶之母指斥子之语,孙权之母以国事托股肱之臣语,虽政权不一,然忠烈之性同。
此为同一作品中之母权人物种种人物语言个性之犯,然而,在不同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母权人物的刻画也会出现这类言语个信相“犯”的情况,唐传奇《崔书生》之母崔氏因子不告而取,故有忧“狐媚之辈”以驱新妇。
《西厢记》崔夫人以“三世不招白衣秀士”赖婚之情由种种都呈现出人母为子思量前途而强拆佳偶的专断个性,此为不同作品之人物语言个性的同一,重复书写和互文转换的背后,虽然短时间作者可以凭借这种文化记忆去寻找和确认母权人物的影子和人物的传承延续。
但是,却不可避免地让读者感受到人物之缺乏个性和独立性,读者在阅读体验中始终以这种熟悉感和掌控力去经验文本,可能对人物产生符号化的认同。
然而到了明清家庭题材之中,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巨变,读者在体验文本不仅能体验到文化习惯延续的熟悉掌控力,同时也在同一类型母权人物和不同类型母权人物的游走中收获溢出期待视野的新奇。
《林兰香》中华书局
在明清家庭类题材作品中,创作者们充分意识到“犯”的不可避免性,然而却力求“犯中求避”,力图在同一人物和不同人物类型匹配以不同的语言,以达到个性和共性相统一的美学效果。
首先是在同一作品中的不同人物之犯中求避现象的语言现象,《红楼梦》中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三人语言均不乏其凌厉情态,如贾母训贾政贾琏之言语、王夫人训金钏儿之言语,王熙凤训仆婢之言语均显其果断犀利之当家主母作风,此为“犯”之同也。
然而三人又各个不同,书中人物语言与人物形象极为契合,正如李渔所谓“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23]]。
《红楼梦》中人物语言,恰恰为一个人生出,移置与他人声口则不伦不类,正所谓“说一人,肖一人”也。
譬如,贾母在贾府之盛时则喜好热闹,其赏小斯喝出“赏”、“该赏”等显出其爽朗乐观的大家气度,到了与大观园子辈以及刘姥姥等嬉乐之际,又显出其慈祥仁爱的老祖母好打趣的慈爱个性,譬如“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40回)
要与黛玉重新糊窗纱儿,叫凤姐“猴儿”、称呼丫鬟为“小蹄子们”(44回)。 这些颇近亲昵的称呼在特定的场合和环境下不仅贴近日常生活之口语,极具戏谑意味,将贾母幽默风趣的个性展露无遗。
然而到了贾府家计萧条之时独撑门户时的话语倒是显得精明算计且老成持重,又遣散余资合理分配又显出其领袖风范。
又王夫人虽掌握主家之权然事事并不经心,如其对袭人之建议将宝玉搬出大观园恰中了王夫人心事,生出一番感慨“我何曾又想不到这里,只是这次有事就忘了”[[24]]其称有事而搁置并忘记“搬出”一事,相比较于袭人的处处留心,显出一番漫不经心的随意本性来。
王熙凤亦是见出不同,她虽有同于贾母和王夫人话语的威严和凌厉,也有不同于她们的明丽爽朗,刘姥姥、冷子兴都称其“言谈爽利”,且还有李纨、薛姨妈等人都曾直言王熙凤口才之爽利。
其次,王熙凤的语言特点还爽利中带点男子气概,完全不同于其她人物的庄重,当然,她也有其典雅的一面,譬如在联诗说出那一句“一夜北风紧”,不论如何也见不得俗来。
可见,在同一部作品中,不同人物类型的人物语言——心理、独白、对话等都会随着环境的转变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而于犯中求避,于同中彰显出差异、于共性中显出个性来。
《红楼梦》封面
其次,不同作品同一人物类型语言的范中求避。
《红楼梦》中贾母与《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奶奶都属于母权人物中之拯救母神的代表,二者都有“散余资”、“散余谷”的相似行为,且二者均为寡母,故二人话语都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属于母权人物中的同类人物。
然而作者在人物身份语言相“犯”的同时力求相“避”,比如同写两人对待子嗣辈,晁夫人在晁源通奸不成反被所杀死时声色俱悲,并且对待与之通奸的小鸦之妻亦是买好妆裹、板木,妥善安排其后事,备写爱子之切与仁义之至。
而贾母对待其子贾赦是“素不喜”,对于次子贾政,她通过对王夫人曲语暗陈“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25]]
其对贾政明嘲暗讽,可见这个素来偏爱贾政的老祖母反而觉得贾政让她受气、不孝顺了,可见,贾母对于自己的儿子多“明嗔暗训”,由此可知,贾母、晁夫人在母子关系的情感依赖方式上是绝不雷同的;
除此之外晁奶奶还表现出贾母所没有斗争性和正义感,贾母作为贾母养尊处优的尊长,再加上其出身显赫的史家,其身份的稳固性可想而知。
然而,晁奶奶却不一样,虽然在家庭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家长而享有绝对权威, 然而在整个家族中她孤儿寡母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其本身的秉性和乐善好施的个性为拔高了她的人格,她以正义与恶势力公然决裂,譬如族中豪强以晁家为绝户意图借吊丧哄抢家产时责怪晁奶奶,晁奶奶决然指斥;
在析分家产之时族中晁思孝、晁无宴二人仗着是头领妄图多得,晁奶奶大义凛然,乃至以正义压人一头,并以理服人;
同时晁夫人也没有贾母身上的富贵之趣,贾母身在富贵荣禄之家,其骨子里体现出贵族的豪气。
在经济方面,其每每要演戏开场后都要打赏戏子,且有贾府查抄后散巨额余资;在艺术品味方面之豪气,其识鉴“石头盆景、墨烟冻石鼎、纱水墨字画、软烟罗纱” [ [26] ]。
凡此种种表现出于与他人迥异的艺术鉴赏力;其待人接物之豪气,对于刘姥姥赞其“富贵命”,却戏称自己为“老废物”晁奶奶的形象在书中刻画得可谓丰满而真实,那么贾母写尽了中国之老祖母形象的可爱、可信与可敬了。
《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楚爱华 著
注释:
[[1]](南朝梁)刘勰著;(清)黄叔琳注;(清)纪昀评;戚良德辑校;刘咸炘阐说. 文心雕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209.
[[2]]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09.
[[3]]诸葛文编著.图说元朝一百年[M].合肥:黄山书社,2011:182-183.
[[4]]罗书华.中国叙事之学:结构、历史与比较的维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7.
[[5]]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47.
[[6]](战国)屈原等著;陈书彬译注. 楚辞[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138.
[[7]](晋)郭璞注.山海经第三册·山海经第十六·大荒西经[M].依宋本校定,项氏群玉书堂:56.
[[8]]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554.
[[9]]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委会.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丛刊·第十辑[M].1985:17.
[[10]]罗书华.中国叙事之学:结构、历史与比较的维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8.
[[11]]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7.
[[12]] 张大可,丁德科主编. 史记论著集成 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7.
[[13]]石麟.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的多角度观照:关于它的潜逻辑过程与逻辑结构[M].光明日版出版社,2016:164.
[[14]]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3.
[[15]]厉平.扁平·人物·圆形——论《金瓶梅》人物性格塑造[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2).
[[16]]曹雪芹著,邓遂夫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M].作家出版社,2006:380.
[[17]]贾文昭,徐召勋.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欣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47.
[[18]]引自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
[[1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422.
[[20]]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
[[21]]西周生著.醒世姻缘传凡例[M].齐鲁书社,1980年版,卷首
[[22]](明)兰陵笑笑生.北图本金瓶梅词话 第四册[M].新加坡南洋出版社,丁巳刊本,第217页.
[[23]]李渔.闲情偶记[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43.
[[24]](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 上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55.
[[25]](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 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45.
[[26]](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 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540.
本文获作者授权“金学界微信公众号”首发,转发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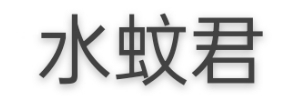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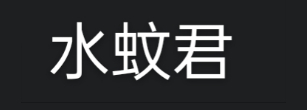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