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在世”、元小说及女性作家叙述权威的建构
——论杨怡芬著《海上繁花》
文 | 何英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小说《海上繁花》的叙事特征及其伦理意义的达成。一是作家通过“身体在世”的感觉主义的细腻描写,使读者意识到身体是意义的纽结,是意义的发生场。人类特有的生命之间的类比与勾连,促使人们反思战争。二是小说本是所具有的历史事件的非虚构及楔子部分的第一人称叙事,表征出小说整体结构的元小说性及后现代性;三是女性作家关于战争题材的叙述选择,以及叙事所折射出的文化中的性别结构,并最终指向人类应怎样建立共同生活秩序的叙述权威。
关键词:身体在世 元小说 女性作家 叙述
一、“身体在世”启动的感觉主义的叙事
“起初我写地狱航船这样的故事,只是想要控诉,可当我慢慢沉浸其中,我想发出的声音,有很多却像是来自那幽深的海底。”①这是小说《海上繁花》中的一段话,作家杨怡芬在接受记者访谈时也有过类似的表达,甚至是反复的强调。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作家启动小说叙事的创作心理的原动力,正是这一对生命被残酷剥夺的感同身受的心痛与怜悯,那种人类特有的生命之间的类比与勾连,使作家选择了生命/身体的视角来完成她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非虚构叙事。在生命结束之前,身体/知觉的感觉主义的叙事便承担起小说关于情感、道德伦理的读者反应的激发与牵引。
“身体在世”②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的一个观点,即知觉总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开始。如果没有身体在世的知觉,就不会有人对世界的感知。小说中关于战俘身体的知觉、以及对知觉反应的描述,直接指向了小说的伦理道德追问。战争的不义、残酷与非人性,正是通过被密闭在船舱里受难的战俘们的身体感觉,以及各种感觉的堆积、压缩和变形的描写,达成其伦理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基础。我们对战争的认识,从如此感性的、身体的、感觉的经验出发,最终在战俘的身体与读者的身体的类比与勾连中形成。在这些感觉主义的细腻描写中,读者同时被迫或积极地启动自己的感受性,体验战争的可怖经验。如果说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那么人为地使他人痛苦就是某种恶。正是认同道德起源于人们的苦乐感觉,道德出自人的感情,小说建构起自己关于战争、关于人类应如何建立共同生活秩序的伦理观。
小说中关于身体感觉的叙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描写准确、细腻甚至华美,从密闭着400人的、各种气味发酵和病菌充斥的3号舱,到逃出舱后在战栗的海里躲避日本兵枪弹的身体的拼命挣扎;在青滨被渔民救起后想起自己曾是文明人的感觉;乃至伊恩三人被救往重庆一路的身体的感觉经验,到最后战争结束,约翰和爱丽丝的幸福日常生活的感觉……整个叙事中前后身体的非文明的、文明的感觉和体验,完成了小说叙述的使命之一:即战争对人类身体的掠夺、压迫和非文明化。比如这些描写:“腿有些抽筋,刚入水的清凉,已经被寒意取代,他竭尽全力抵过了一阵抽筋,必须游得更快些,在更猛烈的抽筋来临之前,游到岛边上,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去,”③约翰此时刚逃离地狱般的船舱,而被鱼雷击中的里斯本丸号正在沉没,沉船周围形成了危险的吞没人的漩涡。这时约翰的身体在世界中了,海中的这个世界不是对立于身体,而是环绕着、包围着身体。约翰此时认识世界的媒介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自己的身体。而读者的心弦随着他的腿在海水里的抽筋而绷紧,难道刚逃出不堪回首的船舱,又要葬身海底了?这是叙事中身体感觉的描述所引起的读者反应。
对战俘约翰、伊恩们受难中的身体感觉的描写,激起了我们对同类尊敬和互相关怀的感情。作者曾谈到:“我写作这部小说的起初感动是对渔民勇敢的钦慕,最后落脚于对长眠于海底的里斯本丸沉船里的年轻人的心疼。”④这种通过想象战俘的身体感觉,想象被剥夺生命权、沉睡海底的800多位年轻战俘的类比与勾连,甚至最终决定了小说的结构走向:后半部分的隐形主角,实在是那海底的八百战俘。⑤关于后半部分800战俘成为隐含的集体叙述声音将在后面论述。小说借叙述者“我”和香织的口吻说出:对自身拥有“生命”体验,特别真实。⑥由此达到一种双重的教育功能,作者先是自己从中受到教育,又使读者意识到小说的教育意义。
也同样出于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东极岛渔民不顾安危、倾其所有地救助战俘,从海里打捞起这些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的英国人。完全忘记了100年前的东极岛正是鸦片战争的战场之一。小说中有多处阿卷父母照料战俘的细节描写,渔民们使他们安眠、给他们吃食和衣物、为他们疗伤。这些细心、细致的照料是从伊恩、约翰们身体感到温暖、舒适的入微的体验来写的。这种从身体的感觉出发来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在伊恩们那里得到延续。当伊恩看到村民被日本人投放的炭疽病毒折磨得双腿溃烂,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取出珍藏的药物赠送村民。他深深懂得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和不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他人的身体体验,勾连起人们类同的身体体验。“生理的身体”由此变为了“交往的身体”,人们由己及人地体验到人生的痛苦和悲欢。
小说以细腻的描写与叙述,使读者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身体的知觉中与世界打交道。身体是意义的纽结,是意义的发生场。我们也是通过身体发现在世存在是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正如小说写道的:卑微的生命,如我们,也许都困在自己的岛上,都在自己的狭窄空间里,可我们一样挣扎着想负起自己那份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都是平等的。⑦伊恩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将阿卷带出东极岛,这是他报恩的方式,也是他觉得自己负有的一个责任。
与身体自由紧密联系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小说中一再写到约翰、伊恩们重获自由后重新找到的一个文明人的尊严。而作为非文明人的体验的描写,比如:“救生艇就在船舷上,他们不放下来,也许,他们连子弹也不想浪费了。有个船员将一条绳子扔到一个战俘面前,战俘待要去拿,那绳子却被飞快抽走,船舷边上的士兵们哄堂大笑。”⑧这种非文明性,除了身体被剥夺,还有人的尊严的扫地。对那些牺牲的战俘来说,他们是死过两次的人。第一次是身体的死亡,第二次是尊严的死亡。
小说带领读者通过返回身体知觉回到前知识的生活世界,由己及人,由人推己,道出一种人类特有的生命之间的类比与勾连,正像梅洛-庞蒂所言,“人类在他特有的生存中,在爱中,在恨中,在个体和集体的历史中,就是形而上学的”。⑨作者也由最初带着“解密”历史往事的心态,却在沉入叙事之后自然而然地用“身体在世”的类比之心完成了小说的伦理叙事与道德追问。
二、元小说及叙事结构
非虚构小说总是具有元小说性。《海上繁花》的整体结构呈现出元小说性。整部小说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前有一个楔子,我称之为“插入文本”。而这里的元小说性就表征在插入文本上,也即几乎与历史叙事同等份量的楔子部分的存在。这些楔子部分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的“我”,一个翻译,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进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纪念活动。“我”同时是一个作家,“我”决定要把地狱航船的故事写成小说。小说文本中也多次提到小说写作的进程、写作的动机甚至情节结构的安排等等。这些表征元小说性的内容进而决定了小说的整体结构。
“我”与日本姑娘香织的恋情,始终作为里斯本丸号事件的后人而受到事件的影响。相恋12年,却因为对方的国族、战争的发起者与受害者身份而致使婚期延宕。然而相恋毕竟是美好的、真诚的,“我”和香织的恋情叙事,也即楔子部分成为与地狱航船事件相互呼应的、作者称之为“明艳与黑暗并置”的结构。这些插入文本与正文之间构成一种直接的对话关系,两个恋人能否最终结合取决于战争创伤弥合的可能性。这些插入文本实际上还像一个个隐含文本,也在促成人们对于战争的思考。它们将时间从眼前穿梭到过去,又从过去推向眼前,以及未来。那些表面文本无法深入的部分,由这些隐含文本来完成。正如施洛米丝·雷蒙-凯南指出的那样,“叙述者如果过于外露,那么他被完全信赖的可能也就微乎其微,这是由于他的阐释、评价和归纳并不总是与隐含作者的标准尺度相吻合。”⑩所以,作家在这里用了障眼法,第一人称的“我”,小张,一个翻译,这个身份几乎可以忽略。读者直接知道这个作为小张的“我”,隐含的正是作者“我”。由此,这些插入文本构成了一种“超表述”行为,一种评价眼光,一种道德尺度。对于小说这种多声道的文类来说,超表述行为尤其显得重要,正是通过这一类表述,叙述者建构起“真实性原则”,令读者接受并理解。这些对历史事件隐含的评价揭示了生而自由的人的品格或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也让读者发自内心地认同并体验活着真好。
元小说的结构还体现在,小说在缝合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上所做的努力。由于小说的事件时间是由过去到现在,即战俘成功出逃的1942年到2017年最近一次纪念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时间跨度。而历史话语是一种表述话语,历史叙事某种意义上说是“硬”而“实”的,需要作家如历史学家一般对历史档案文献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检索和查阅,在此基础上才能亦步亦趋的重构;也就是说,文学虚构叙事是一种“生成”式的、缺乏真值评价的施为话语体系,而历史叙事是一种“认知”的、具有真值功能的话语体系,两种话语目标的不同导致阅读承受着分裂和断裂的风险。诚如苏珊·吉尔哈特所言,历史与虚构虽然并非独立的王国,但它们永远不会完全合并。⑪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断地强化这种差异,历史叙述与虚构叙事之间存在着永不统一的界限。历史毕竟是对已经确立为事实的事件的叙述,尤其是面对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虚构叙事是不可能的。如何处理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对于《海上繁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文本类型和体裁的差异。作家在写作之时就面临着区分叙事化与虚构化的难题,而如何区分的结果,也会由文本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形成叙事的循环。同时还要应对的叙事难题包括,虚构与历史互相渗透所产生的某些叙事世界,这是《海上繁花》这类有历史本事的小说怎么写所面临的共同议题。
结果是历史小说或故事的施事星河被分割为两个子集,一个由虚构人物组成,他们有历史的对应者;另一个由没有历史对应者的虚构人物组成。⑫这在《海上繁花》的叙事中得到证明,一方面约翰、伊恩们,甚至阿卷父母和阿卷等人物,呆在实有其人的子集里,他们跟里斯本丸有关的真实经历不容施事话语偏离真实;另一方面,“我”和香织的跨国恋,包括香织的奶奶、家人们,呆在没有历史对应者的虚构人物子集里,而小说的完成就需要将两个子集里的人物及叙事有效地缝合起来。正如小说中写道:“历史总是干巴巴的,我喜欢浸润了水分的故事——即便明知它掺杂了虚构,或许还夹带了作者的许多私货。”⑬这是因为,某种意义上说历史话语要到达“真实界”,需要诉诸“情节编排”的文学式叙事,包括历史的细节、情绪、体温和表情,正是这些内容使历史叙事比之纯粹的历史纪撰具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和说服力。也正因此,将历史叙事的“硬”与“实”转换为虚构叙事的自由与传奇,这是一重叙事考验。
而当时空转入当下,历史叙事瞬间转变为类似于新闻体的小说叙事,操作方法又变为现场采访、忠实记录,而由此形成的文体必然带有新闻色彩。新闻体叙事与文学虚构叙事同样存在文体差异,东极岛渔民搭救英军战俘的心理动机、道德依据,是作家通过实地采访得来的;里斯本丸纪念活动中阿卷等村民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与约翰的重逢与互动,也只能采用新闻体色彩的笔触,这又是一重叙事考验;这个容纳了历史非虚构叙事、新闻体叙事、文学虚构叙事的文本,便成为展现元小说、后现代拼贴的实验场。
新新闻体小说于二战后在西方兴起,这种“事实性叙事”满足了人们对于细腻实录的需求。它与历史叙事的不同在于,它描绘现在的形象。其价值在于以文献式散文代替了“倒退的”与社会无关的虚构,从而变得像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强大。《海上繁花》以典型的虚构叙事的手法与新闻笔法糅合起来,其视点不断、多次的转移,由一开始的伊恩一家到约翰的视点,再到伊恩的视点、再回到约翰的视点(指除楔子部分以外的小说主体部分),其间还大量穿插他们的内心独白。可以说,19世纪叙事史以来行之有效的诸种手法都在被运用,但这种新新闻体小说显然有对既有叙事的翻新,它穿梭在现实与虚构交互的时空里,打乱了人们对单一虚构叙事的阅读习惯。它追求一种超越虚构的“真实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多种叙述类型的并置、碎片式拼贴,使整体叙事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即叙事的主观性、混杂性和零散化。
三、女性作家叙述权威的建构
作家通过一种非历史性的倾向,即赋予历史以生活肉身的写法,提供了女性作家书写战争题材的某种写作策略。在这里,“女性主义”意味着对主体经验的强调、对文本意义的追求,还意味着将各种范畴混杂起来的后结构主义倾向。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的观察会受到其主体立场的影响,那么作为女性作家来处理一个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就必定会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叙事景观。“我写得最得心应手的应该是涉及女性和日常生活的部分。”这种女性作家的视角,选择将叙事看成一次整体的修辞行动,拉开叙述者与她自己的距离,用繁复的视点、声音、空间等等,建构起女性作家关于战争的文本叙述。这个文本所引起的读者反应,包括情感的、伦理道德的、性别意识的诸种反应,都可见出女性作家的叙事在文化中的性别结构方式,如萨丽·罗宾逊所说:“我关心的是性别如何通过叙事过程产生出来,这个文本是如何为读者和使读者建构男性意识或女性意识的?”
比如这样的叙述:“你忘在床格里和梳妆台上的东西,我都放进小箱子里了,和那些底片在一起。”⑭在此之前,敏妮将卢瑞秋母亲在婚礼仪式上赠送给她的金手镯等贵重首饰悄悄留在了卢家,她要跟随父母回英国了,她想为爱人留下这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毕竟中国还在战乱之中。但卢瑞秋却细心地发现了,仍将这些首饰装在了敏妮的行李里。类似这样的细腻描写,充实了整个文本。这些细碎的、充满感性与情感的细节,都凸显了女性作家在文化中的性别结构方式,更彰显出女性作家建构叙事权威的伦理观:人们之间的相爱,完全可以跨越种族、国族,甚至是仇恨。作家试图写出相爱的人们相处的细节,并以此为模范,为人们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秩序,提供感人的文学景观。
小说中的叙述声音,“我”是一个男性,但真实的作者是女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设置。我们所熟知的海明威式关于战争的硬汉叙事,以及战争的男性叙事,某种意义上已形成一种关于战争叙述的垄断。似乎战争是男性的,一个女性的叙述者天然不占优势,而一个男性叙述者的设置则是一个不错的叙述选择。但隐藏在后面的实际上的女性作家的叙述声音、叙述眼光,那种“本真”的女性声音,便与小说中的男性叙述者声音产生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令人感兴趣的叙事学议题所在。
这个故事对于作者来说,显然是一个“异故事”,作者不可能亲身参与其中,她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那么,作者型声音的叙事是惟一之途,如何使作者型叙述令读者像在读一个作者亲身参与的“同故事”一样亲切,“插入文本”就是她的叙述策略之一。作家籍此建立起小说赖于取得读者信任的“生活空间”,并制定出她能借以活跃其间的女性作家的叙述定律;建构起关于身体的感觉主义的话语权威,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而让其他意义保持沉默。比如这样的叙述:“经过这么多年海水淘洗,舱底的污秽,都被洗净了吧?被海水和钢铁封存的身体,会是怎样的样貌?这么些年,舱口还保持着封闭吗?”“直到四五年前,他才开口和家人说“里斯本丸”和集中营的事情,……不要把黑暗带给家人。”⑮这类叙述仍然将身体的感觉主义的叙事贯穿下来,从而达成作家关于战争的道德追问。
在作者型声音的叙述之外,作家主要是启动了让历史中幸存者用个人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法。因此,这是一个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同时出现的小说文本。前者建构了虚构作者“叙述”的声音,后者则形成了某个人物“摹仿”的声音。而这两种叙述模式负载着不同形式的权威。它们互为背反:作者型叙述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却显得更具有可信度;这是为什么读者在看“我”和香织的恋爱故事时,不用怀疑其真实性,直接明白其为虚构的小说;而个人型叙述往往被当做自传体,但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被认为是名正言顺。如小说中约翰、伊恩的视角及经历,他们的内心独白,都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如果说启动个人声音叙事,让历史中的幸存者开口说话,并不总是女性作家的特权,那么杨怡芬在建构个人声音的叙事时,则投入的是女性作家的视角、感觉以及对细碎的生活世界的热衷与擅长。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还有一种叙述声音的存在,那就是作为东极岛所有救过里斯本丸号沉船战俘的渔民们的叙述。即第三种叙述模式,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存在。它们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是各种声音的集合。如这样的语句:“这岛民的祖先中,很多就是被救上来后在此安居的,下雨天,大家凑在一起搓麻绳,讲的最多的是救人的故事。救人一命,天上一星。”这种集体叙述的声音,传达出渔民们救人的心理动机和道德依据。第三部分中阿卷和香织之间的对话,阿卷的视角和叙述,实际上也是一种代表东极岛渔民叙述的集体话语叙述。这些集体话语叙述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杨怡芬对里斯本丸号历史事件叙事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再现,而是要在作家与读者之间达成某种关于伦理道德的共识。这在文本中体现为杨怡芬《海上繁花》对最终的伦理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一再追认。正如小说中写道的:“在坏的时代,我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个好人呢,这其中肯定有好多好人的。⑯只要人类还要延续下去,共同的前景设想与展望就是必须要正视的伦理建设。
一位小说家在写作并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对话语权威的追求:为了赢得读者、获得听众,进而取得社会的尊敬和赞同,建立广泛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小说当做文化事业来阅读,实际上,读者关于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始末,正是通过作家的叙述获得事件之外更多元的价值,包括有关世界观的观察与体验。这个展示性文本给予作家在虚构话语和历史的边缘地带创造叙述声音的机遇,而作家的创作也在这个过程中促成了自己虚构叙事的权威。读者从中受惠,激发起关于人类应如何建立共同生活的秩序,建构起新的人类关系诗学的沉重思考。
叶芝的诗句说,人类所体验的是“过去之事,眼前之事,将来之事”。这部小说就贯穿了这三种时间。里斯本丸号沉船的过去时间、“我”和香织的现在时间,以及我们共同的未来时间。小说中写道:“即使战争已经过去,但某一天战争重来的话,我们就自然接受它的残酷?”小说仿拟身体/心灵对时间环境的再现,目的是“这世界上,必须有人记得战争,那才会明白和平不是天然之事。”⑰而这正是这一部以历史纪撰为副文本的非虚构小说的社会政治或伦理意义。
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中提出,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步积淀心理规范,而人们的每一行动都处在彼此依存的网络中,这就意味着必须考虑同处这一网络中的他人,从而形成一套文化意义上的自动化机制。文明的进程需要人类不断自我修正、完善这一机制。小说通过一种教育或自我教育的叙事伦理,令读者意识到文明的进程值得我们一再反思非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作者深入到历史的纷纭复杂中去,赋予历史体温、表情,尤其是血肉的感觉,只有经历了这个生活世界的身体的痛和不自由,我们才能懂得活着的真谛,才能由此建立一种新的人类关系的诗学。“因为世界的过去时代实际上并不是由礼仪、公文、争执和抽象的人填充起来的,而是到处有活生生的人们。”⑱
任何的历史叙事都是对过去的重构。这种重构并不能完全复现过去,历史本来就是不可复现的,作家只不过重新创造了一个令读者相信是历史事件的故事。但我们相信伊恩、约翰是真的,相信阿卷父母以及东极岛上救人的渔民是真的,甚至也相信“我”和香织是真的,因为这些人物通过虚构话语的施为性,生成了一个活在小说中的人物世界。读者可以接近这个人物世界中的他们,赞美或怜悯他们、谈论或议论他们。而这正是小说叙事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湖州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①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16页。
②[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6页。
③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81页。
④钱报读书会|舟山人杨怡芬谈《海上繁花》:我的初心,吾土吾民
⑤钱报读书会|舟山人杨怡芬谈《海上繁花》:我的初心,吾土吾民
⑥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55页。
⑦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40页。
⑧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81页。
⑨[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小说与形而上学》,载《意义与无意义》(《梅洛-庞蒂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页。
⑩[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⑪[美]卢波米尔•道勒齐尔:《第七章 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载《新叙事学》,[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马海良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⑫[美]卢波米尔•道勒齐尔:《第七章 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载《新叙事学》,[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马海良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⑬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⑭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32页。
⑮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97页。
⑯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18页。
⑰杨怡芬:《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62页。
⑱[美]卢波米尔•道勒齐尔:《第七章 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载《新叙事学》,[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马海良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本文发表于《当代文坛》2024年第3期,原题名为“身体在世、元小说及女性作家叙述权威的建构——评杨怡芬《海上繁花》”。
编辑:肖媛龄
二审:樊金凤
三审:胡晓舟
《海上繁花》新书上市 | 重返现场,是不够的
杨怡芬:我的小说,要有一个坚实的内在
献给那些在泥淖中盛开如花的女性 | 张楚《云落》新书上市
2小时居然就可以读完一本书?!
张楚:我知道县城里有很多秘密写作的人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海上繁花》
- 随机文章
- 热门文章
- 热评文章
- 身旺的土命,未来几年,能赚到钱吗?
- 保姆级教程,番茄小说推文如何顺利申请授权?如何赚取收益
- 番茄小说的成功秘诀:微短剧背后的流量机制,揭示流量之路!
- 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番茄小说《斩神》等作品上榜
- 完美世界影视牵手番茄小说 头部IP作品《何不同舟渡》影视化提上日程
- 2024起点十大玄幻小说,新颖刺激,探寻奥秘
- 科幻小说 | 睿乘密码(七)
- 聚焦解读“中国密码”,第四届七猫现实题材征文大赛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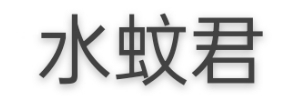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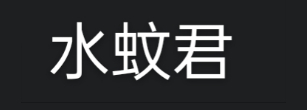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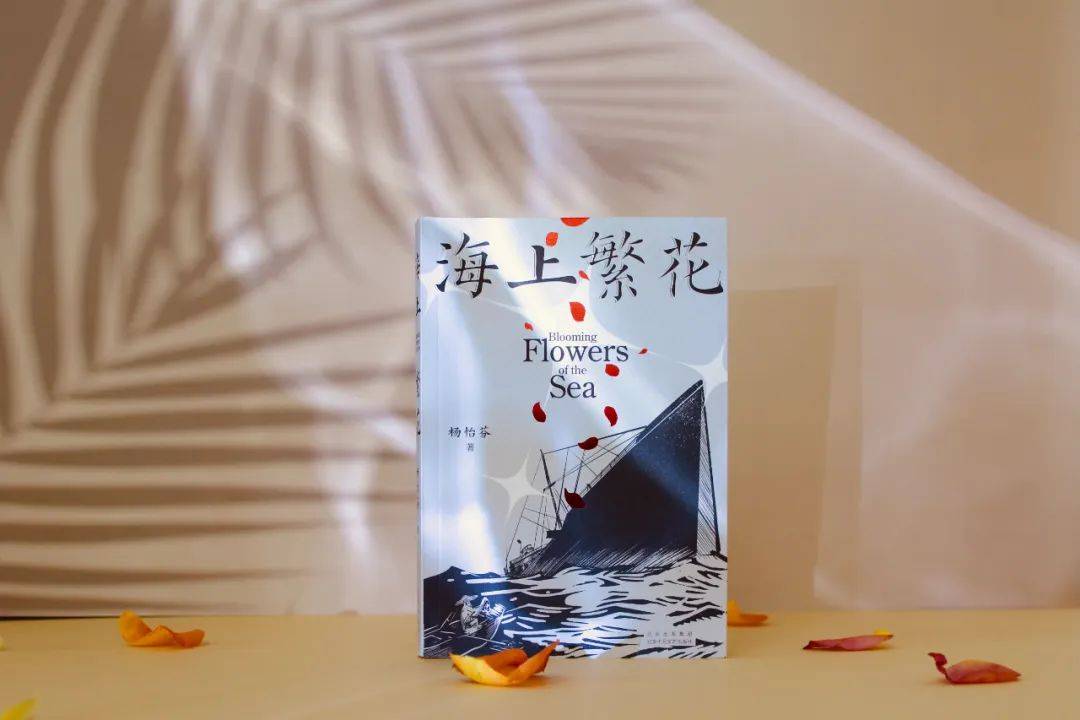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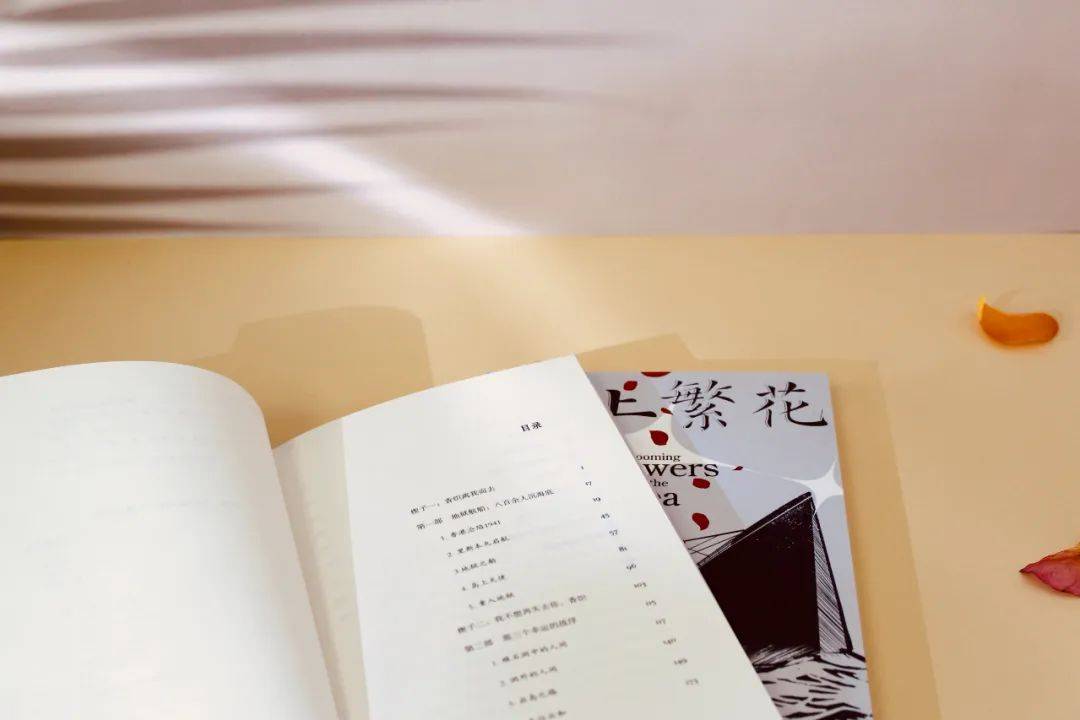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